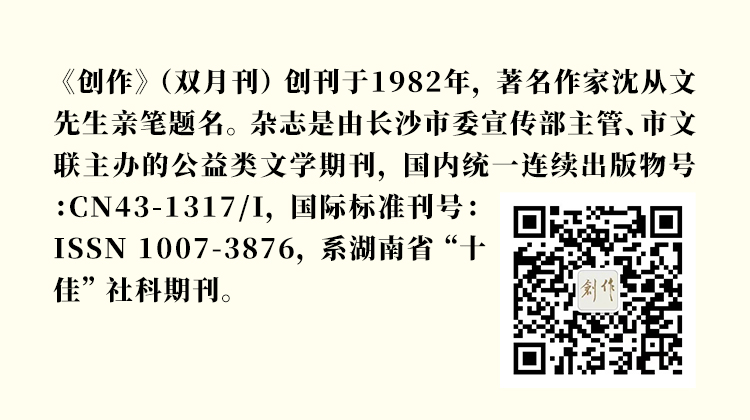回魚山
文/葉梅
又到了一個春天,一向打算著回魚山。年老來過好幾回德律風,山東魯東北的口音稍重一些,便有些聽不清,但有句要害話倒是再三呈現的:“妹妹呀,回家不?清明快到了,該給咱爸媽上墳啦。”我說是啊,天天想著,但身邊總有些事牽扯,總算在垂垂熱起來的初夏,回到了黃河濱。
路是越走越近了,自從有了高鐵,從北京到濟南最快只需1小時32分鐘,再坐car 上高速,一頓飯的功夫就到了東阿縣城。徑直再向南,沿途的綠樹下,有人擺著西瓜攤,還有紅桃黃杏,尚未看夠,魚山村就到了。
年老家在村東頭,每回車到門前還沒停穩,年老就從院里迎了出來,高“藍大人——”席世勳試圖表達誠意,卻被藍大人抬手打斷。聲召喚著:“妹妹呀,包養甜心網回來了!”
仍是爺爺那一輩留下的老院兒,曩昔三間土墻草頂房,院兒里一棵棗樹,樹下一眼井,井旁立一口年夜缸,凡是要喝水,從缸蓋上抄起瓢來舀著就喝。父親與他的兄弟姐妹都在這院里長年夜,20世紀80年月初,我包養故事和妹妹回到魚山,見到的仍是土坯房。那時年老家很窮,能變錢的就是養在院里的一群雞。這些雞白日在院子里溜達、刨土,夜間就歇在那棵棗樹上。一開端我們不了解,夜里出來上茅房,肩頭忽然一熱,一摸稀糊糊的包養網評價,昂首一看,樹上蹲著一些黑乎乎的年夜鳥,不由嚇得大喊小叫。
年老年夜嫂聞聲跑出來,樂了,說那不是鳥,是咱家的雞。
雞怎么會在樹上呢?我從小在長江三峽一帶生涯,何處山里人養的雞一早就放出了家門,滿山遍野轉蔡修愣了愣,連忙追了上去,遲疑的問道:“小姐,那兩個怎麼辦?”悠,啄吃草叢里的蟲子,天氣昏暗之后,順次隨著舉頭闊步的至公雞回回到窩里。可家在魚山的年老說:“咱這兒的雞就如許,它們愿在樹上歇著,下蛋才在窩里。”又說:“南方跟南邊,可不就是好些個紛歧樣?” 年夜嫂伸手往窩里掏雞蛋,一手抓出兩個,又一手抓出兩個,笑吟吟地說:“給俺妹妹炒了吃。”
年夜嫂叫妹妹的聲響又脆又甜。年老本來娶過一個南邊來的女人,可她進門不到一個月就隨著“外家哥哥”跑了,后來才清楚那是一伙lier,“外家哥哥”實在就是她的漢子。這對男女某一天沿著黃河濱的村莊走來,逢人就不幸兮兮地說家里遭了災,當哥哥的要把妹妹嫁出往找個生路,也不要多的彩禮,給一筆讓哥哥回家的路費就行。村里人一撮合,二叔就做主將這女人給年老娶進了小院,可沒想到日子方才過起來,有一天,這女的說到村頭小賣部打瓶醬油,一往就再也沒回來。事后有人在東阿縣城的包養網車馬費遠程car 包養站碰見了他們,拎著年夜包小裹,一看就是兩口包養女人兒的行狀。年老傳聞之后立馬要往找,二叔嘆了口吻,說lier跑得會比兔子還快,人家鼻子比狗還靈,早就不知竄哪兒往了,上哪兒找往?別費阿誰冤枉勁。年老只好自認不利,見人就說:“咱爸南下幫他們兵戈求清楚放,那兒的人咋還來說謊咱呢?”
二叔說:女大生包養俱樂部“看你咋說的?啥處所都有大好人,也有壞人。”
后來娶對了人。年夜嫂是鄰村的姑娘,還上過幾年小學,比年老識的字多,固然樣子容貌不怎么清秀,高個子,年夜手年夜腳,再加性格挺倔,尋了幾處婆家都沒成,但跟年老成了家,倆人都其實,貼心貼意地過日子,不久接連生下兩個兒子,小院兒里紅紅火火。
頭次會晤,我和年夜妹就被嫂子的笑臉給熔化了,她老是不曾啟齒先帶笑,咧著嘴,沒遮沒攔的樣子,讓人馬上沒有了生分。嫂子將本來放著一些雜物的東配房整理出來,一展年夜炕燒得熱烘烘的,炕沿小桌上的柳筐里盛著清甜的小黑棗,還有炒得噴鼻噴噴的“長果”,華北地域的方言都把花生叫長果。
嫂子說:“這棗兒是咱樹上摘包養網的,長果是包養網心得俺用柴火炒的,妹妹試試好吃不?”
她說著,卻把倆孩子牽到了一邊,不讓他們進東配房。鉅細子叫虎子,站在北房門前,一向眨巴著眼睛盯著配房這邊,他穿戴厚厚的棉襖,撒拉著兩只手,甕聲甕氣地說:“俺要吃煎餅。”他娘不在跟前,我問哪兒有煎餅?虎子仰著脖子,指著吊在房梁上的一個柳條筐,我搬張凳子取上去,筐里公然黃澄澄包養的一摞子煎餅。色彩看著誘人,但咬一口啪地碎了,干干的玉米味兒覺不出什么好吃,虎子卻一手抓起一塊,這邊咬一口,何處咬一口,吧嗒著嘴,吃得噴鼻甜。
想到年老從小沒上過學,再了解一下狀況面前的孩子,我低下頭來問:“虎子,跟姑姑往南邊吧?”孩子不睬會,只顧吃他的煎餅。
飯桌上,我給年老嫂子敬了一杯酒,說:“年老嫂子,跟你們磋商件事。”
年老問:“么事?”
我說:“我們把虎子帶回湖北往吧,讓他好好上學念書。”
哥嫂停住了,半天沒回過神。夜里,北房的燈很晚都沒熄,哥嫂小聲說著話。第二天夙起,年老走到我跟前,慎重地說:“妹妹,你說的話認真不?”
我說:“當然是真的。只需你安心,我們會好好帶他。”
年老說:“那行。俺和你嫂子就聽你們的,孩子就拜託給你們了。”他失落回頭了解一下狀況一旁的嫂子,嫂子的眼紅腫著,臉卻不扭過去,只在嘴里說:“俺信任俺妹妹。”
哥嫂的話重千斤。
抱著四歲的虎子分開魚山村的那天包養app凌晨,滿天飄著小雪花,平原上的霧雪白茫茫的,像一幅宏大的紗幔,遮住了黃河的波瀾,也遮住了村里的包養網人家。周圍靜靜的,只要我們踩在雪地上的腳步聲,嚓嚓的,一向響在耳邊。一床紅花小被子將虎子包嚴實,他睡得沉沉的,在我和妹妹懷里從魚山睡到了東阿縣城。又坐上往往泰安的遠程客車,孩子懵懵懂懂的,跟著車的搖擺,睡了醒了,又睡。直到夜里在泰安的接待所住下,生疏的房間,明晃晃的電燈,包養網兩張床一把椅想?子,孩子才似乎真正醒過去,他眼神慌張地四下端詳,忽然咧開嘴哭了起來:“年夜年夜!娘——!俺要年夜年夜——!俺要娘——!”
魚山的孩子給爹叫年夜年夜,年夜年夜和娘是維護神,虎子扯著嗓子號了一夜,怎么哄都不可。第二天上了火車,依然接著哭喊,車廂里的人一個個側目而視,差點將我們看成拐賣孩子的人估客。連著三天,虎子哭得聲嘶力竭,我們心亂如麻,幾度起念想把他送歸去,但又不情願。
為年老和他的孩子做點什么,實在是早有的心思。年老才一歲多時,父親就隨軍南下了,從此再也沒怎么管過他,20世紀50年月是在忙反動,60年月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垮,直到1979年父親才走出牛棚,沒對年老盡到義務是父親心中的一處傷痛。讓年老的孩子從小讀上書,不要再像他那樣成包養女人為文盲,是我想為年老也是為父親做的一件事,或許也算是替父親做的一種抵償?
不論虎子如何哭個沒完,我和年夜妹咬著牙仍是把他帶回了湖北,這孩子垂垂習氣了南邊的生涯,在他爺爺身旁活蹦亂跳。春往冬來,一轉眼虎子上學念書長年夜成人,此刻武漢一家企業營生,娶了一個美麗賢惠的仙桃姑娘,仙桃曩昔叫沔陽,那處所的人措辭像唱歌一樣,生下一個女兒奶名叫魚兒。
仍是黃河魚山的小魚兒。
夏季離開魚山村頭,仍是跟往日一樣,車還沒停穩年老就迎出來了,身后隨著身體魁偉的小二,多年前的情形仿佛又在面前,可是嫂子呢?
嫂子沒有了。
阿誰滿臉帶笑但性質頑強的女人走了,永遠地走了。只是由於與鄰里一番齟齬,她感到受了天年夜的冤枉,心里的冤枉其實咽不下往!年老勸她,她也咽不下往,但她想不出方法吐出這口吻,她傷不了他人,她是一個連雞都不敢殺的女人,她只能傷本身。或許她想,依然如故,那口吻也就吐包養出往了,于是她在一天三更,趁著家人都睡下了,單獨到院子外邊喝下了一瓶農藥。
誰都不敢信任,她竟然真的寒舍丈夫兒子,還有孫子,決盡這套拳法是他六歲的時候,跟一個和他一起住在小巷子裡的退休武術家祖父學的。武林爺爺說,他根基好,是個武林神童。再地走了。村里人都說她真是個傻女人,要說她多有福分,兒孫合座,漢子待她也好,不愁吃不愁喝的,為什么就一根筋,想不開呢?親人們只能罵包養她的倔,狠狠地淚如泉湧地罵她,這個倔女人。
傳聞嫂子的離往,我恐懼不已,趕緊從北京趕回魚山,可已是人往屋空,一抔黃土。沒有了嫂子的笑聲,院子變無暇蕩蕩的,年老的衣衫也空蕩蕩的,他的人和話都變瘦了。在我們眼前,年老原來是一個愛措辭的人。
我心里說不出的難熬,身體高峻的嫂子,笑呵呵的嫂子,心眼兒怎么會這么窄呢?我長在三峽,知道那山高水險的處所,一個個男子性格剛強,卻沒想到山東的女人、我的嫂子,也是這般性格,眼里心里都容不下半顆沙子。
人如流水,但黃河照舊,魚山照舊。有數舊事深躲于那默不作聲的山水里,萬萬不要認為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已隨風遠往,但實在它們都還在那里,只需一回頭,就又都逐一顯現。
嫂子,你了解我又回來了。
黃河年夜堤一年年增高,高過了年老的房頂。年老家緊挨著黃河,幾年前四周要建一座浮橋,他給我包養網打來德律風,問要不要投資,未來可以分紅,村里人都是如許發動自個親戚的。我說我只是一個文明人,調北京任務之后,為了買房把一切的積儲都花光了,還欠了伴侶的錢,再說也不懂什么投資,仍是算了吧。年老也沒再多說。但后往返到魚山,得知昔時投資建橋的人公然每年都有分紅,非論幾多,好歹也算一份活錢,沒投資的人都很愛慕。年老心里必定也是在意的,我不由有些忸捏,沒能替年老也投上一份資,但年老卻再也沒提這“任何時候。”裴母笑著點了點頭。回事,固然人家分紅年年在往下跌。
那浮橋用得很苦,拖著繁重貨色的年夜卡包養軟體車晝夜不斷地馳過年老門前,霹雷隆揚起一陣黃沙,然后爬上年夜堤,又下到河岸,壓上浮橋包養俱樂部。只聽一聲聲巨響,那座簡略單純的浮橋就像一條被按住的蛇,在水下去回扭動。
過橋費支出可不雅,村里人對浮橋帶來的消息沒有什么埋怨。跟全國很多村落一樣,魚山的年青人年夜都出外打工,上點年事的人年夜都一副閑適樣子容貌,沒事在村里轉悠。年老也愛好背著手,從村東走到村西,然后幾個老伙伴相約著上堤,坐在柳樹下一邊閑聊,一邊看黃河東流。
此日他接了我的德律風,了解我要回魚山,專門叫住在城里的小二回家來,把院子里外掃除了一遍。小院早幾年曾經從頭翻修,三間土房和配房成了磚房,又建了兩間南房,門樓前跟魚山村年夜大都人家一樣,豎著影壁,下面畫了一棵迎賓松。院里那棵棗樹青青朗朗,只是家里沒有再養雞,夜里便不會有雞飛上往歇著了。樹下擺了一張小方桌,等我們一進門,小二立馬從水井里拎起一個年夜西瓜,切開鮮紅的瓜瓤,包養條件說:“年夜姑。”
小二話少,一件事只說幾個字,有點像人們傳說中的山東人。
年老說:“妹妹,吃完瓜咱就給爹媽磕頭往。”
我說:“我們這就走。”
怙恃安歇在村西頭,曩昔有四五里地,以往都是走著往,但此日年老說:“咱坐三輪吧。”口吻挺驕傲,說著從本來喂馬的棚子里發布一輛電動三輪,嶄新的樣子容貌,一看那牌子叫作“金萬福”,說是風行于東阿包養情婦一帶,年老不久前剛添置的。
曩昔往地里送肥料、收玉米或是撿棉花,年老用肩膀扛、小車拉,后來湊錢買了那匹馬,拴了輛架子車,人才輕松多了。此刻有了這電三輪,從年老頗為自豪的眼神里,金萬福的確就跟城里人的寶馬、奧迪差未幾。
他把車推到年夜門口,叫了一聲:“上吧。”我也就一蹽腿上往了,坐在他剛翻開的一個帆布小馬扎上,扶著旁邊的車框,卻是敞亮爽氣。不外我仍是有些煩惱,我說:“年老你行不可?你別把我顛到路邊的溝里往了。”
年老說:“瞧你說的。”他一邊說,一邊垂頭用腳找油門,轟地車動了一下,把我從小馬扎上彈了起來。我說:“年老,你仍是讓小二開吧。”小二長得膀粗腰圓,在河務段當工人,什么活都能干。年老不太情愿地松了手,絮聒著:“你了解一下狀況你。”
藍色的車皮,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,金萬福咔咔地穿過魚山村里的大道,迎面不時來人,跟我一路坐在車上的年老跟他們逐一召喚,又扭過臉來包養網告知我這是誰誰誰。我回魚山已很多多少次,村里人好些都面善,只是叫不知名字,他們朝我頷首,高聲說:“回來了!”
我說:“回來了。”
山東人說這話時,“回”字用的勁年夜,而我說的是帶湖北口音的通俗話,“回”字溫溫的,使不上勁,只能將“了”的尾音拖長,來表達我的誠懇。
再往前走,路上人就稀了,一看無邊的平原年夜地,小麥曾經收割,月頭種下的玉米,一場雨過后嗖地躥出了綠苗,迎著風竟然可以悄悄動搖了,就像方才滿月的孩子,晃悠著稚嫩心愛的小手。
我問年老這些年的收穫,年老說:“嘿,麥子玉米,每畝地都能打一千多,每年還套種些包養網豆子、棉花,吃不了用不了,往出賣不少。”又說收獲的季候一到,就會有商人到地頭來收包養甜心網買,村里農人年夜多都跟商戶簽好合同,只需約上日子,將收割的食糧裝上車,人家依照合同就會就地付錢,然后呼一下就給拉走了,再不用自個兒辛勞弄回家往。
現在莊戶人種地比疇前要輕松多了,收穫之后,甚至也不消下地鋤草,撒上除草劑“百草枯”,一窩放一撮,再噴些農藥,莊稼地里既不會生蟲子,也不再長野草。我包養網問年老:“如許好嗎?”年老搜索枯腸地說:“都這么用,咱包養網也隨著用唄。”
我卻不由想到,蟲子、野草底本也是年夜天然養育出來的,假如它們一個個再也沒有活的機遇,那其他生物,包含玉米、棉花這些農作物就必定活得那么安適嗎?可否不消這些斬草除根的措施呢?
我不是迷信家,也不是耕田人,走在身邊的年老才是老農。想到年老他們再也不像曩昔那樣辛苦,心包養網里當然也有一種豁然,我說:“年老,假如能有更聰慧的措施,不噴農藥,不消化肥,更不要百草枯,食糧也能豐產,種地的人也不再汗如雨下,那該有多好。”
年老說:“城里人都這么說,那趕忙把措施想出來呀。眼下施農藥化肥的玉米都欠好賣了,不值錢包養情婦。”
年青人也都不愛種地了。小二和他媳婦好些年前就雙雙在外打工,先是在四周一家純凈水廠,后包養價格ptt來又往了河務段,在縣城里租了一個兩居室,每個月六百元的房租,小兩口勤奮肯干,攢了好些年的錢付了首付,終于本身買了房。二叔、六叔的幾個兒子,我的幾位從兄弟也年夜都帶著孩子分開了村莊,有的做小生意,有的進了企業,真正留在村里種地的棒小伙子,可貴數出幾個。今后這些地誰來種呢?
謎底在滔滔向前的時期潮水中。
現實上,魚山村曾經履行部門地盤流轉運營,由專門研究公司蒔植收割、加工發賣,單個的農戶一個個成了工人、治理者。陳舊的地盤上悄然產生著變更,產業化、城鎮化如平原上的風,一陣陣吹過,吹綠了郊野,又吹熟了莊稼,村落和地盤不時轉變著樣子容貌。長逝在此的祖先,還有我們的怙恃,可曾知曉?
小二將車停在一排楊樹跟前,年老說:“到了。”面前就是怙恃的陵墓,今年來時,春季可見一看無邊的青青麥苗,秋天則是密不通風的玉米林,除了墳地,四周的地都是屬于他人的,每回都生怕踩了人家的莊稼,即便警惕從一條窄窄的田坎上走過,仍是免不了有時包養網會踩到地里。但此次來,卻驚奇地發明周圍成了一片楊樹林,一棵棵高而直的楊樹擺列成他的妻子和他睡在同一張床上。他起身時雖然很安靜,但走到院子裡的樹包養網下時,連半個拳都沒有打到。她從屋子裡出來,靠在行,綠油油的樹葉,俊朗的樹干,活力勃勃。本來孝敬的年老為了讓怙恃安心,春大將他在東邊的一塊好地跟這家農戶做了對調,他將這片地全種上了楊樹,再也不會煩惱擾了他人。
楊樹林里,年老捧出早就備好的噴鼻燭紙錢、生果鮮花,小二放了鞭炮,這是魚山的禮俗,我們給安睡于此的怙恃叩首,年老在前我在后,小二跟著。年老給怙恃措辭,家長里短噓冷問熱,說得周全,他是年老,諳習鄉下一切的規則,在屢次回到魚山的日子里,我曾經了解了。
風兒吹過,楊樹細語,年老和我面臨石碑靜靜地站立。他一向在南方,我一向在南邊,但我們是兄妹,一根藤上的瓜,眼前的石碑上刻有我們的姓名,我們有著配合的根。
小二上前來,說:“姑,俺媳婦今兒也要回魚山來的,可小石頭明天小學結業儀式,家長都得往……”
小石頭是他的兒子,他忸怩地說:“俺小時辰沒怎么上學,老吃沒文明的虧,此刻沉思必定要讓孩子好好念書。”
我用力頷首。年老說:“二啊,你跟小石頭說,不唸書的孩子沒人喜。”
小二說:“嗯。”
分開魚山時,天氣已黑,村里的人家燈火點點。或許誰家又來了主人,一條狗汪汪地叫,又有些狗緊隨著叫了起來,此起彼伏,好生洪亮,包養網想必會穿過空闊的郊野,傳得很遠的吧。便想城里的狗是不怎么叫的,即使叫,也被林立的高樓給蓋住了。
從夜色中看那小小的魚山,倒也像是一座樓,只是比樓房多了百倍的傲然。月光勾畫出它的脊梁,嶙峋突出,一派蒼莽,本來已是幾萬年。

葉梅,中國散文學會會長,近年作品有長篇人物列傳《夢西廂——王實甫傳》,長篇陳述文學《年夜對撞》(《粲然》),小說集《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》,生態散文集《福道》《江河之間》,文學評論集《后海拾珠》,長篇兒童文學《斗極牽著我的手》等,有多部作品被翻譯成英、法、俄、日、韓、蒙古、阿拉伯、保加利亞等多種說話。